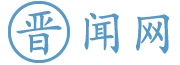耿彦波是周浩的纪录片《大同》(又名《中国市长》)里的主人公,1958年出生,2008年至2013年在山西大同担任市长,2013年调任太原市长。在大同当市长期间,耿彦波接受了周浩的拍摄。周浩纪录下了这位中国“拆迁市长”的日常,完成纪录片《大同》,该片获得第5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和圣丹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。
耿彦波在任时,被媒体称为“作风强势、毁誉参半”。由于题材特殊,《大同》在世界各地许多影展都引起轰动,但是周浩一直很少谈论有关《大同》的内容,理由是耿彦波还在任,「不希望过度消费被摄者」。
如今耿彦波正式卸任,D纪录特别转发2016年punchline对导演周浩的专访,以飨读者。
周浩曾经在一次演讲中,形容纪录片工作者犹如牆头上的苍蝇,又像遥远的上帝,与被拍摄的对象保持著一定的距离,不干预,安静地、隐形地看待所有事情的发生。即使暂时换个位子,从摄影机后走到了摄影机之前,周浩仍然保持著这个原则。他安静地站在角落裡,说起话来语速缓慢,音量特别低,必须要集中注意力,才能听得见他在说什麽。
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低调到你几乎看不到、听不见的瘦小中年男人,连续以《棉花》、《大同》两部作品,获得第 51、52 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,他也因此写下了金马奖史上,第一个连庄最佳纪录片奖项的历史纪录。
《大同》是周浩在 2001 年从记者转行之后,所拍摄的第 10 部作品,主角是作风强势、毁誉参半的前任山西省大同市长耿彦波。全片描述耿彦波在任内,大量拆除大同市区内违章建筑,雷厉风行地进行整修道路、修复及开发古城等各种大型工程。抱持著「大同只有这一次机会,衝上去就衝上去了」的悲壮心情,耿彦波把这个千年古城几乎刨开了一大半,五十多万市民因此被迫搬迁。随著耿彦波在 2013 年被突然调职,《大同》至此也嘎然而止,留下一个比剧情片更加曲折震撼的结局。
由于题材特殊,《大同》在世界各地许多影展都引起轰动,甚至获得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,但是周浩从来不曾随片出席,连去年的金马奖颁奖典礼也缺席了。他的理由是「不希望过度消费被摄者」,「主要是因为他还在任,如果因为这部片子,而他受到影响,那我心裡就会有结,也许以后都不能再拍下去了」,「因为我的目标不只是这一部片子,而是我的余生还要继续拍下去。我也不觉得我不去就是对的,但这样,也许我会好受一点」。
这一次到台湾,等于是周浩第一次直接面对观众。几场放映下来,周浩觉得台湾观众的反应,并不会过度政治化,「这样挺好的。」他说,过去曾有人看完《棉花》后,问他对于纺织工业链未来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,「我回答得出吗?我答不出」。
周浩说,《棉花》就是用棉花为主题,串起这些普通人的故事,《大同》也一样。「城市需要发展,需要什麽样的政府官员?这是一个一直在探讨的问题。最后未必要有结论,但是探讨的过程中,会留下一些东西。」而《大同》既是那个探讨的过程,也是过程中所留下的「东西」。有些台湾观众看完《大同》之后,直接联想到台北市长柯文哲,「有人建议说,应该请柯P来看,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拆巨蛋。」周浩说,这个过程,就是他所乐见的,「当你看完片子,你会联想到你自己的城市,你自己的生活体验,这样就很好」。
周浩说,《大同》在世界各地影展放映,许多迴响是他无法想像的,观众会在影像的叠加中读出一些味道,觉得「这里是不是别有用心呢?」比如片子里出现很多狗,很多人就会有联想。事实上,只是因为城市不断施工,所以街上很多流浪狗,到处都能看见,「我下意识就会去拍一拍,拍了之后觉得拿来做镜头过渡也不错,但是就会被过度解读」。但从另一方面来说,「你说我放这些镜头的时候,有没有『潜意识』?也许有,那是各种机缘凑在一起出现的结果」。
从 2001 年的《厚街》开始,一直到现在的《大同》,不论拍摄的主题是什麽,周浩的作品总是保持著相同的特徵:没有旁白,配乐少之又少,情节与情节之间大量留白,在平铺直叙中又带有某种无法言说的朦胧诗意。例如在《大同》的尾声,耿彦波坐车正式卸下市长职务后,在车上默默流泪的片段让人印象深刻。车子轻轻摇晃,挥手欢送的人群在后窗裡渐渐变小,安静的车内只有耿彦波与他的眼泪。不过周浩说,他并不懂诗,他也觉得《大同》不像诗,而是一种直白的纪实体。
《厚街》,将镜头对准东莞厚街一位出租屋裡的外来打工者,在那个地方,「上演」着砍人、讨债、失业、爱情等,乃至非法接生等等的事件。
最初剪接师看到耿彦波在车上流泪的这段素材,很直觉地就垫了一段抒情的音乐上去,却遭到周浩直接反对,他认为音乐有一定的导向,会诱导观众思考,「某些段落本来没感觉,但是音乐一配上去,立刻你就哗哗哭了。我说这种哭不真实,我反而会建议把音乐去掉,因为你被带偏了,你做了一个局,让别人掉进这个局里去,有点蛊惑人的感觉。我觉得这种东西在纪录片里是忌讳的」。
从摄影记者到纪录片导演,周浩从事报导相关工作,已经超过二十年。或许正因如此,周浩在许多方面,都让自己刻意保持距离,始终谨守著一个「度」字。在《大同》拍摄过程中,他紧跟耿彦波拍摄长达一年多,但是两人之间始终保持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,当耿彦波说「你别拍了」的时候,周浩也从未拒绝过他的要求。
「我跟市长之间的距离,一直都是比平时看到的,稍微近一点而已。他有时说你别拍了,那就是他的私隐。因为你的最终目的是要一直跟下去,你并不希望在短时间之内关系破裂,而无法继续。这也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的基本」,「人与人之间需要分寸,如果(靠得太近)我会不舒服,那表示被拍摄者与观众都会不舒服。观察人时,有一定的距离,有个『度』反而会增进了解,不至于被表面蛊惑,忘记初心,反而忘记事情本真的基础。所以我会提醒自己,得有『度』。」
问题是,「度」这个东西,多宽多窄,多远多近,「没有标准答案,没有老师,没有裁判,完全只能靠自己内心的感受决定」。经过多年历练,周浩已经得出自己的心得,「跟做人做事一样,就是别让自己难受。人最大的敌人不是观众,不是政敌,不是狐朋狗友,而是自己。你怎么过自己心里面那个坎儿,如何把手上的事情做下去」。
「有人问我拍片时哭不哭,我说现在不哭了。你如果要问我上一次哭是什麽时候,我都想不起来了。」周浩说,二十多岁的时候,很容易受各种因素影响,容易投入感情或感动,可是像现在,看电影如果觉得眼眶湿了,他会马上反问自己「这是生理反应上的感动?还是发自内心的感动?」,「它真的让我这麽感动吗?这值得哭吗?我是不是被什麽力量左右了?」他认为,这种时候,反而是反省自己最好的时机,「可以告诉自己,不要从众,不要别人说什么,你就感受什么」。
周浩说,比如美国的观众在看完片子之后,都希望影片能有个结果,而且他们一定每次都会问同样一个问题:「导演,解决方法是什么?」他们(观众)会希望,「你要告诉我一个解决方法。他们习惯了被给予,我不觉得这样好。我不会走那条路」。
在《大同》里,周浩并没有下任何判断,也未引导观众往何处思考。他同时并陈了耿彦波大同市民的生活片段,一边雷厉风行视察工地,一边可怜兮兮控诉政府;一边被请愿民众团团围住,一边又大骂政府扰民。总是在观众即将同情某一方的时候,天平又立刻倾斜向另一边,整部影片不断呈现出的,是一种沉默而隐形的拉扯。
「影片构成是需要不同力量的,没有对手戏不会好看」,周浩说,所有片中的辅助角色,都是来让主角更加立体的力量。影片中的所有片段都来自真实,然而最后呈现出的结果,却又是一种经过精细的计算,「真实是不可能被还原的,如果你够真诚,只能够趋近」,「纪录片只是相对的真实,我从来不认为它会是毫无瑕疵的真实。那是自欺欺人」。 |